疫情下的社会分析:深圳国际交流学院学子跨学科人文沙龙
来源:国际学校招生网
时间:2022-01-27 16:12:14
【引言】

21世纪10年代结束了,它被画上了一个太过仓促且含糊的尾声。今天,自新冠疫情爆发已近两年,这是短暂的两年,一切都改变得太快,作为个体的我们却活得太慢。
我们见证了许多——那是全球化时代最后的回响——但又没能记下多少,我们很少注意到翻涌的历史表面之下被盖过去的那些声音。
社会学老师(人文组组长)Richard到场参与分享
Mr Driscoll 强调了举办关于“社会不平等”话题研究沙龙的重要性,因为该话题在分析当代问题时无法回避,而在当下疫情的特殊时期更具有特殊意义。

为什么我们选择社会不平等这个话题?
“疫情衍生的远程社交、远程学习等新政策引发了与社交网络、社会复原力、高效治理相关的新问题...... 新冠疫情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在全球范围内增加了经济、文化和社会上的不平等,这已经成为未来社会学理论和研究、以及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主题;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我认为,是对埋藏的既定社会结构和我们整个社会的更深入研究。”
——Maggie Liu, sociology ambassador

本次深圳国际交流学院的跨学科人文沙龙从经济,哲学和社会学的三重视角深入分析了疫情后不平等的议题。
【学科干货总结】
Economics
分享人Felix和Brian
本次人文沙龙中,Felix和Brian主要阐述了疫情前后的不平等现象长期趋势,并且对疫情下的不平等进行了定性分析。
分享开始,Brian先对广义的不平等与经济上的收入不平等进行了定义,方便大家更好理解后面的内容。随后,Felix对COVID-19 的增长所导致的不平等进行了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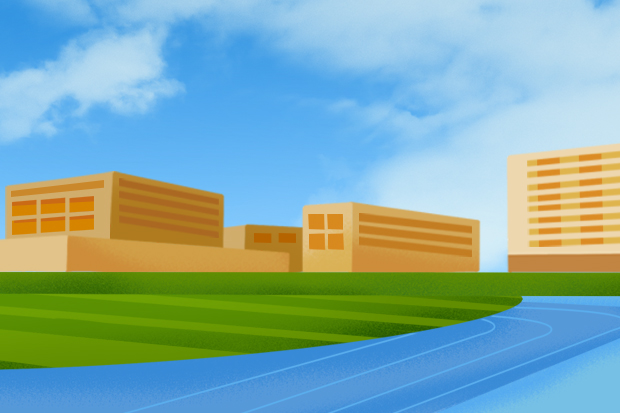
由于当前数据、研究的量有所不足,本次分享在对疫情不平等的分析上主要采用的是定性分析。分享中Felix和Brian 将主要的不平等诱因分为三类——公民健康系统的不完善、核心医疗资源稀缺与信息的不对称、还有工业停摆所导致的失业率增加和收入减少。
根据伦敦政经学院、世界银行的分析,年轻人、女性在本次疫情中受到了更多的不平等的影响,其中女性在承担着许多无报酬工作的同时还在疫情期间成为了更多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总的来说,疫情较为严重的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让我们看到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马太效应愈加严重;同时,女性群体在疫情下所受到的不平等尤为严重。

诚然,疫情对不平等的加剧影响是巨大的,但是纵观近几年,我们可以发现不平等问题并不是仅仅是疫情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存在并且日渐恶化的问题——自近几年开始,全球的不平等就一直在增加。
以我国为例,自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一直有所增加,但是由于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提高,并没有造成负面影响;21世纪初,中国的基尼指数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一直到2015年出现反弹。
根据IMF的分析,中国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教育不平等、地区不平等、产业不平等以及医疗资源不平等这几个方面。无独有偶,根据英国政府统计,英国的收入不平等(以最富1%的收入总占比为指标)在近十年由于经济发展与金融业在次贷危机后的复苏逐渐增加;同时,自近年起英国的基尼指数也开始反弹,已经超过了英国70-80年代的平均水平。

除此之外,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基尼指数长期趋势一直是较大的增长;根据发表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的文献与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早在2010年左右美国的收入两级分化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美国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前(1928)的程度。
总体来说,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近十年来全球的不平等现象愈加严重,如基尼指数的关键指标的增加让我们意识到不平等现象已经对全球发展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而疫情这样一个黑天鹅事件并不是长期不平等加剧的核心因素,但它的确对于不平等有着非常大的加剧作用。

经济老师Cheong和Henk在听学生分享
Philosophy
哲学主讲人Winnie
本次分享主要以政治哲学中生命政治的研究范式去解析健康码的内涵,希望回答一下三个问题:在政治哲学的语境中,健康码的定义是什么?在这样的理解下,健康码对生命政治中的权利结构产生了什么影响?最后,我们是否应该/能否在这样的权利范式下做出一些改变?需要强调的是,本次分享并不致力于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希望提供一种思考路径供大家参考和讨论。

首先,本次分享借用了“从「健康码」到「文明码」:数字时代如何安顿「余数生命」”(吴冠军,2020)一文中对健康码的定义,指出健康码是一种以科技的形式(即二维码)为免疫共同体划出界限的途径。在这个定义中,“共同体”是由其「排斥」(exclusion)而非「包含」(inclusion)所定义的。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使用的「想象中的共同体」一概念来指代「民族主义」,这个「共同体」的定义是被其「排斥」界定的。例如,要厘清「中华民族」的定义,事无巨细地列举「中华民族」的内涵,如“这是一种拥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的民族”的工作,考虑到共同体的多元性、可变形与准入性,是几乎不可能成功的。

要定义它,一个更简单的方式是通过厘清「界限」(boundary),如”中华民族排斥了美国人“。(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在做的工作并不是在事无巨细地列举其排斥的内容,这不过只是重蹈覆辙;相反,这种定义在强调“排斥“本身,即”界限“和”准入门槛”的存在。)那么,在今天的语境中,健康码达到的目的则是“排斥一切的可能是不健康的人”——如密切接触者、经过过高风险地区的人,等等。
也就是说,健康码搭建的边界构建了一个「免疫共同体」(community of immunity),而搭建共同体的方式则是通过技术,即二维码。在这里便出现了政治哲学中两种研究范式的对象:前者是「生命政治」(biopolitics),而后者是「科技政治」(technopolitics)。

紧接着,本次分享简要介绍了这两种政治哲学进来愈加普遍的研究范式(生命政治与科技政治)的主要研究对象,以及该研究对象在健康码的引入之后产生的变化。首先引入了福柯对权力的定义相较于以前的变化,即从「毁灭性权力」(destructive power)向「建构性权力」(constructive power)的转型。 在中世纪,权力主要以「剥夺人的生命权」的方式存在,以震慑大众,避免某种行为。其中一个例子是刑法。相反,福柯观察到,另一种形式的权力,即「建构性权力」在我们的生活中愈加常见,该权力的表现形式在于(有意或无意地)构建起一种行为模式,或是提供一种行为模式的可能性,而非避免一种行为模式。它是「支持性的」(supportive),「建构性的」(construct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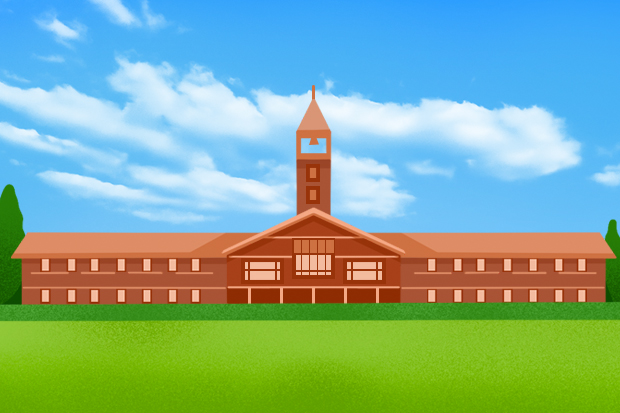
由此,「生命政治」内的权力运行,便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建构性权力,即一种支持生命存在的权力(the power to sustain life)。
国家通过建立医保、医疗器械科研支持、医院等医疗设施投资等方式支持个人的生命存在,而健康码则也是其中一种生命政治的运行模式。
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结合大数据等科技政治,健康码的生命政治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当有科技的参与的时候,生命政治的处理对象便从「肉体人」(corporeal person)变为了「数字人」(digitalised person),即在科技系统中有所登记的,由一条条信息组成的个人。也就是说,在科技政治和生命政治的联合作用下,作为一名「数字人」是“被生命政治保护”的前提。

而在健康码这一体系下,「数字人」的内涵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数字纯粹生命」(Digital Zoe, or Digital ‘mere life’)变为了「数字社会生命」(Digital Bio, or Digital qualified life)。
这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数字生命,例如婴儿刚出生的时候需要在医院建立档案,记录血压、身高、体重等等;而后者则指社会学意义上的数字生命,例如拥有健康码绿码是进入公共场所——如商场、交通工具等,以及进行社会生活的必要前提。这一转变通过在疫情期间逐渐渗入生活的健康码普及率展现出来。

最后,本次分享简要分析了这一分析下健康码的影响,即个人层面的隐私权,以及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首先,当健康码,或者说生命政治的目标与隐私权相冲突的时候,应该如何做出取舍?在紧急状态下(如疫情),以及非紧急状态下,这种取舍是否应该有区别?我们思考了一种观点,即把疫情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即每个人与每个人之间的战争——相对比,去合理化把生命政治置于隐私权之前的选择。
在霍布斯的理解中,每个人由于恐惧,只能够以防御战争或是攻击性战争的方式自保(后者可以建立权威,以此来保护自己);而这种观点把病毒与“人与人之间时时刻刻可能发生的战争”作比较,体现出两者兼具的不可预测性,因此就像是霍布斯对其自然状态的解决方案——签订契约,建立国家政权,在一个类似的“每个人与每个人之间的感染”的情景下,解决方案也可以讲生命政治的处决权交予国家,通过健康码优先生命权,牺牲隐私权。

最后,分享提出了这种观念的一个更宏观的后果,即国家之前的敌对与保护主义。在分享结束之前,Winnie最后提出了一个阿甘本的概念,即「余数生命」(remainder-life),来思考其对生命政治以及健康码造成的双重挑战:一方面,余数生命本身在系统中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余数生命的不可完全清除性也对生命政治项目的完全成功提出了质疑。对于如何处置余数生命,其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对“优先生命权于隐私权之前“的挑战方式,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Sociology
社会学主讲人Maggie
由于各国对疫情防控政策避免接触的考量,以及教育工作保持进展的重要性,网络远程教育逐渐被各地学校采用。但除了当下短期问题的解决,从多种数据分析上看,远程教学无疑加剧了教育领域的数字鸿沟现象(Digital Divide)。
在全球教育数字化的进程中,不同社区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和新科技设备的拥有程度以及应用程度有一定差别,使得教育资源落差进一步两极分化。根据Sutton Trust的数据报道,32%贫困学校的老师反映,超过五分之一的学生缺少用于课堂的电子设备——缺少基础设施的资源将直接导致远程教育无法展开;只有惊人的5%的公立学校教师表示他们全部的课堂都有良好的互联网环境——卡顿的网络意味着教学效率和质量的下降;更有66%的学校只能使用自己的内部资源来为学生购买IT设备。这些直观的数据直接导致了基层社会教育质量的低下,从而加剧了贫富之间的教育不平等鸿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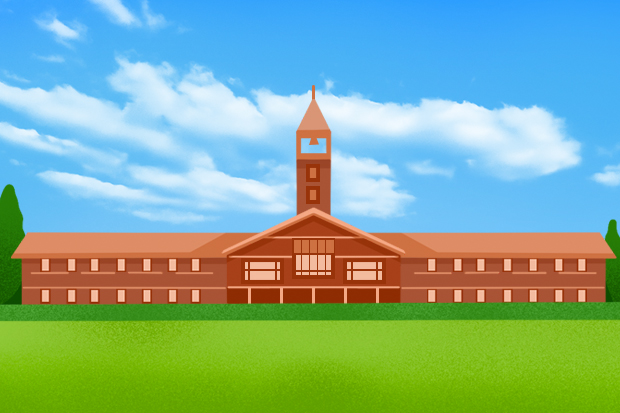
若看向鸿沟的另一极。私立学校可以成为很好的例子:学费,社交圈等前提构成了进入壁垒,筛选出有经济基础的,以中产阶级家庭为底的社会阶层。
调查结果显示,来自私立学校(意味着富裕家庭)的学生成功参与线上课程的可能性是其他学生(来自公立学校等)的两倍。这些家庭能够提供更好的网络条件,基础设备,应用指导等等,因此对于以数字为基础的线上教育,他们能够直接地享受远程教育发起者所期待的便捷。
同时,更有数据显示,家庭年收入超过100000英镑的父母(为中产阶级或以上)于疫情期间平均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超过100英镑。由于线下和老师沟通的机会的稀缺,这些资金可能被用于寻求课外的学术帮助,也可能被用于购买线上学习资料,加强网络设施等等。

不论如何,经济基础对远程教学提供的优势显而易见,从而更大程度上形成了与公立学校和基层家庭的对比。
在呈现清晰直观的数据和分析之后,Maggie向我们介绍了更为隐蔽的教育不平等(invisible inequality)——隐性不平等的概念。由于疫情期间绝大多数学习过程都在家里完成,家庭的学习环境变得格外重要。经过调查,超过四分之三的研究生父母和60%的本科生父母有充足的自信来指导孩子的学习。相比之下,拥有A level或者GCSE学历的家长中,只有不到一半对辅导有信心。

综合来看,疫情后教育不平等的发展是具有社会性的现象,而不是个人独立选择的结果。个体的行为所表达的不止是他们本身的意愿和选择,更是社会结构推动力的功劳(human agency and social structure)。
在宏观层面上,阶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等社会因素,都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所带来的生产效益在更加依赖于社会纽带的线上教育时期被进一步放大,并附带上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加成,使不平等被更准确地定义为社会各方面的催化成果。

正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社会学的任务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社会世界中埋藏最深的结构,以及确保其复制或转化的“机制”:
to uncover the most profoundly buried structures of the various social worlds which constitute the social universe,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s” which tend to ensure their reproduction or their transformation.

在面对不平等时,我们不仅需要用情感去应对,不仅需要内部思考自我选择,也需要向外部寻找集体的共通点(collective practice),个人及政治。
更多深圳国际学校相关资讯,可到本网站查看!
免责声明:文章内容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





